
从来没有哪个朝代像宋朝这样饱受争议,有人说它积贫积弱,有人说它文明辉煌。北京大学赵冬梅教授认为,从1063年英宗即位,到1086年哲宗初司马光离世,二十四年间,宋朝政治由盛转衰,堪称“大宋之变”。
本书以司马光的后半生为线索,推演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政坛风云,深入濮议之争、王安石变法、司马相业等历史细节,以人物为经,以事件为纬,充分展现韩琦、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文人政治家在历史大变局中的抗争与博弈,再现共治时代末期知识分子的荣光与屈辱。以抽丝剥茧的分析推理,典雅流畅的语言,探究大宋之变的错综因果和历史真相,揭示朝代兴衰、帝国统治的深层根源。
编辑推荐
这是一个朝代的转折史,作为君王,他们奋发进取:行新法,败安南,收河湟,改制元丰,伐夏开边……却无法阻止国家衰亡
这是一群有识之士的时代悲歌,作为臣子,他们名震千古:韩琦、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却难解当下危机
君臣遇合之际,他们积极寻求变革,却终将改革变成政治角力,将北宋推向危亡的深渊!
1.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宋史专家、“百家讲坛”特邀主讲人赵冬梅治宋史之作。讲透“大宋之变”的深层根源和历史逻辑:在以皇权为根基的帝制时代,宽容政治消亡、君臣共治打破,北宋政治走向不可逆转的腐败。
2.以人物串联历史,以细节关照全局。以推动了历史发展的枢纽性人物司马光后半生行迹为切入点,来勾勒北宋政治的演变轨迹,还原北宋由盛转衰的历史真相,探讨帝制王朝的政权格局与历史命运。
3.深入历史过程,还原历史事件中的“情与理”。对许多宋代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如王安石变法、司马相业等,重新回到历史情境中进行同情之理解,从宋代的历史和当时实际的效果中予以评析,为读者提供新的看待历史的方式。
4.以史料为据,从人性角度,充分还原了北宋君臣在历史大时局的命运与选择。
5.附有《大事记年》《官制简表》,人物关系、历史脉络清晰可循。
6.高品质装帧设计:精致内外双封,五色印金工艺,护眼双胶纸,收藏级的印装品质。
作者简介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曾任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特邀主讲人。致力于宋代制度、政治文化和历史人物传记的研究、写作和传播,主要著作有《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武道彷徨:中国古代的武举与武学》《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千秋是非话寇准》,译著《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
精彩书评
如果历史学家会讲故事,那就没小说家什么事儿了。司马光无疑是北宋的“文化灵魂”之一,他后生的二十四年,正好见证并参与了北宋由盛转衰的转折。历经英宗、神宗、哲宗三朝的政治风云,读者似乎能跟着时间的推进,目睹大宋的政治资源是怎样一点一滴地耗尽,让“共治”的理想变成黄叶满地,借用书中标题,“没有赢家的战争”。作者“对人事的深刻理解”让这本书通俗而不媚俗,易读而亦耐读,成为难得的写史佳品。
——杨早(著名书评人)
文献工夫很足,洞察很深刻,但并不故作高深,叙述流畅,文采飞扬。对宋朝为什么会从仁宗时期的包容走向神宗时期的专制,宋神宗、王安石做了什么,应负怎样的责任,交代得很清楚。
——姜鹏(百家讲坛主讲人)
二十四年,是如何将一个王朝由盛世拖向末世?作者历史学家赵冬梅选择了一个主角作为这个转变时代的见证者,这个人就是司马光。这位《资治通鉴》的编撰者,以史学家名垂后世,但在过去的六十年中,也背负种种不堪之名,他被斥责为守旧、迂腐、不知变通的顽固派,偏执地阻扰王安石发起的变法新政,而后者则被寄予了复兴大宋的希望,甚至宋朝走向衰亡的原因,也被归咎于王安石变法在保守派的打压下失败。
但在本书中,却以详尽的史料对这一教科书式的定说提出了可能是*雄辩的一次质疑,而这次质疑直指惯常被论者所忽视却又是问题的关键之要,那就是权力。一如作者在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礼仪也好,理财也罢,表象之下的本质正是权力。
皇权的本性就是集中与支配,司马光的所作所为必然如蚍蜉撼树,也就注定了其失败的终局。权力这头猛兽已然被神宗和王安石君臣携手从笼中释放出来,数四三番以聚敛为能事的变法已经让君主尝到了集权的甜头。当司马光终于身登执政之位时,他已经是身负重疾的垂垂衰年,尽管他穷尽心力试图驯服权力的野兽,却只是孤军奋战。一如作者所引用司马光zui后时光的那句自况“如黄叶在烈风中”,忧其危坠而终于危坠,他的力挽狂澜也随着他的死亡而告终,他悲剧性的结局也兆示着这个失去了缰绳的王朝,将骑着权力的野兽奔向死亡的终点。
——李夏恩(新京报书评周刊记者 )
目录
第一部 父子君臣,1063—1067
1 父死子继
2 帝后 母子 天下
3 强撤帘
4 式微歌
5 濮议:父亲名义战
6 把名字刻入石头
7 没有赢家的战争
第二部 旧邦新命,1067—1069
8 新皇帝二十岁
9 “大有为”锋芒初露
10 一朝天子一朝臣
11 话题人物王安石
12 四月谈话
13 理财争论出延和
14 司法分歧起阿云
第三部 风云初变,1069—1071
15 开封山雨欲来
16 马王初较量
17 王安石的胜利
18 皇帝爱韩非
19 去意决绝
20 青苗法红线
22 登楼不见山
第四部 长安不见使人愁,1071—1085
23 勇敢者的墓志铭
24 独乐园中狮子吼
25 新法得失
26 书局风波
27 遗表真情献大忠
28 神宗的眼泪
第五部 黄叶在烈风中,1085—1086
29 开封的呼唤
30 言路何难开
31 “黄叶在烈风中”
32 “司马相公”的体制困境
33 神宗旧相
34 僵局
35 “奸臣”去
36 政治中的政策
37 病榻上的宰相
38 复仇与和解
39 人间最是宽容难
40 葬礼与哀歌
精彩书摘
父死子继
新皇帝疯了
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1063年4月30日)的半夜,仁宗皇帝突然驾崩。第二天,四月初一,宰相韩琦(1008—1075)宣读大行皇帝《遗制》,命皇子赵曙(1032—1067)即位,尊皇后曹氏(1016—1079)为皇太后。
《遗制》就是皇帝的遗嘱,它的主要功能和核心内容当然是交代后事。尽管如此,仁宗《遗制》的一头一尾还是流露出强烈的个人情感。《遗制》的开头简单地回顾了仁宗的帝业:“我继承大统四十二年来,一度担心自己资质浅薄,不足以担当祖宗留下的宏图大业。幸而战乱平息,百姓安居乐业,我何德何能,得以致此?!……”在结尾处,仁宗感叹:“当死亡与生命交界,只有圣人才能参透它的奥秘,幸好我大宋天命不堕,后继有人,更要仰赖各位文武大臣悉心辅佐,补充新皇帝的不足。我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这篇《遗制》当然不是仁宗的亲笔,而是仁宗去世之后翰林学士王珪(1019—1085)的代笔之作。然而,如果仁宗在天有灵,应当也会同意《遗制》中所表达的不舍得与不甘心。作为一个皇帝,仁宗十三岁即位,在位四十二年,撇开刘太后摄政的十年,仁宗亲掌大政三十二年,他和宰相大臣们一起,领导宋朝摆脱了西北边疆的危机,保卫了国家安全,重建了宋一辽一西夏间的国家关系平衡;对于宋朝建国以来在官僚特权、行政体制等方面积累下来的弊端,仁宗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改革意愿,经过庆历新政的演练磨合,仁宗与改革派之间最终达成了更深刻的信任与默契,在仁宗晚年,改革派重返朝廷,各项改革措施稳健推行;对于列祖列宗以来所形成的宽容的政治风气,仁宗身体力行,他尊重士大夫,容忍并鼓励批评,在仁宗的朝堂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的政见和争论的声音,对于国家的各项政策措施,官员们各抒己见,激烈讨论,最终得到更加符合国家利益的决定。仁宗不是一个英明果断、雄才大略的君主,但是,在他的治下,宋朝也称得上国泰民安、百姓富足。嘉祐(1056—1063)作为仁宗最后一个年号,在宋朝人的历史记忆中,将会散发出越来越迷人的光彩。
如今,新皇帝上台,开封的宫阙换了主人,大宋王朝的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
新皇帝赵曙,史称英宗。新皇帝的作风如何?开封政坛翘首以待。开封人都听说,这位皇帝陛下,从小喜欢读书,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衣着简朴,为人谦和有礼,看上去就像是个读书人。况且,他即位的时候已经三十二岁,有足够的社会经验了。所谓“国赖长君”,看起来,大宋王朝也算是所托得人。
最初的四天,一切安好。
英宗是四月初一即的大位。初二日,他颁布诏令,大赦天下,百官普加一级,厚赏三军。初四日,他任命首相韩琦担任仁宗的山陵使,负责先皇的丧葬事务。一应政务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新皇帝显得谦虚老到,他尊重先帝留下来的各位宰相大臣,从不直呼其名,宰相报告任何事情,他都要详细询问来龙去脉,然后再做决定,而对于他所做的决定,大臣们私底下都表示赞赏。其间发生的一件事情甚至让宰相们感到了一丝惶恐。按照惯例,那些在最后关头为先皇治疗的倒霉的御医要受到处分。其中的两位,是在三月初二才从外地调过来的,奉御日浅,有人便为他们求情说:“先帝最初服用这两位的药,还是有疗效的。不幸到了这个地步,这是天命,不是医官能决定的。”没想到年轻的皇帝顿时变了脸色,问道:“听说这两位是各位大臣推荐的,对吗?”宰相们说“是”。新皇帝又说:“那我就不敢说什么了,还是请诸公亲自裁决吧。”最终,在十二名受到处分的御医中,只有这两位被贬到了偏远地区。这件小事让宰相们心下悚然,再不敢小瞧刚刚上任的皇帝——他知道他的权力是什么、有多大、在哪里。皇帝虽然是新的,但是并不嫩,所作所为符合他的年龄。
权力交接平稳,新皇帝政务实习及格,一切平顺,诸事大吉。然而,谁都没有想到,这种状态只持续了四天。到了四月五日,事情忽然发生了大逆转——新皇帝疯了!
这一天,天还没亮,宰相大臣们正在待漏院等待上朝,忽然接到宫中消息:皇帝突染重病,朝会取消,先皇的治丧活动暂由宰相代理主持。皇帝究竟怎么了呢?宰相们得到的密报是,皇帝头天晚上忽然发了狂症,不认识人了,说话颠三倒四,语无伦次。前一日在朝堂上好端端的皇帝,怎么进宫去睡一觉就变成了这般模样?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皇帝受到了怎样的刺激?还有,更重要的是,皇帝的病还要持续多久?
整个外朝都在打探,在猜测。就这样,从初五挨到了初八。按照礼官选定的日子,初八是仁宗大殓,遗体正式移人棺木的日子,这是作为儿子的新皇帝必须亲自主持的仪式。皇帝病情是否能够好转,到时自见分晓。
结果又怎样呢?更糟了!英宗皇帝病情加剧,当着众臣的面,“号呼狂走,不能成礼”。情急之下,宰相韩琦丢掉手里的哭丧棒,拉起帘子,冲上前去,牢牢抱住皇帝,这才稳住了局面。接下来,韩琦叫来宫人,让她们把皇帝扶进宫去,小心看护。安顿了皇帝,韩琦又率领着两府大臣觐见太后,经过一番紧张的商量之后,最终商定,以英宗的名义下诏请求太后“权同处分”政事。根据太常礼院拟定的规矩,届时太后会和皇帝一起出现在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
时隔四十一年,大宋王朝再一次出现了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只不过,上一次皇帝十三岁,而这一次皇帝三十二岁;上一次是奉了先皇的遗制,而这一次却是皇帝病狂,太后不得已出来主持局面。
活了三十二岁都好端端的赵曙,怎么做了皇帝反倒发起疯来?难道是压力太大,不胜负荷?还是别有隐衷?还是说曹太后对于英宗的即位心存保留,所以她有意逼疯英宗,以便自己掌权?一时之间,疑云笼罩宫城,英宗的皇位乃至开封的稳定都成了变数。
……
前言/序言
前言
一 细节 真实 偶然性
本书所讲的,是北宋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时代的历史,叙事时间上接《司马光和他的时代》(生活书店,2014年)。那本书从司马家世一直讲到仁宗朝结束,是以司马光的成长为主线的真、仁两朝政治史。本书从仁宗养子英宗委屈纠结的即位开始,一直讲到哲宗初年司马光含恨离世。
荒唐的英宗四年给北宋政治造成了深度伤害,财政困难加剧,官僚集团裂隙横生。作为英宗之子,血气方刚的神宗因而背负了为父亲和血统“正名”的责任,必欲“大有为”。开疆拓土、治礼作乐都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财政困窘其奈何?王安石“乃能趋赴,以向圣意所在”,[1]施展理财之术,创为青苗、免役诸法,以朝廷而行商贾之事,与富民争利,多方敛财,乃使国库充盈,有效配合了神宗的拓边事业。王安石与神宗先后相继,变本加厉,“一道德”,“同风俗”,斥“异见”“人言”为“流俗”,弃“祖宗之法”于不顾,自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拜相至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驾崩,十六年间,“靡然变天下风俗”,把仁宗朝独立思考有担当的士大夫改造成为工具性十足的官僚。理想主义在消逝。北宋前中期朝堂上“异论相搅”的宽容风气,君主体貌大臣、存恤“大体”的“和气”氛围,宰相大臣、侍从台谏敢争是非的独立精神,都在崩解消散中。“危辱时代”即将来临。司马光抗争不得,自熙宁四年(1071)起,退居洛阳十五年,成就了伟大的《资治通鉴》。
神宗驾崩后,哲宗少年即位,神宗之母太皇太后摄政,邀请司马光还朝主政,更化调整。司马光对于“神宗的官场”缺乏基本认识,对追随者毫无约束意愿,对国家的实际状况缺乏调查研究,对政策调整缺乏通盘考虑,无队伍,无手段,无能力,无经验,空怀一腔热血,以皎皎之身投诸滚滚浊流,执政十六个月即抱憾而终,徒留一曲失败英雄的悲歌。
司马光身后,官僚集团的矛盾白热化,陷入“恶性分裂”(解释详后),宋朝政治跌入“危辱时代”。士大夫因内斗自我消耗,集体迷失方向,失去了制衡皇权的力量。皇帝和宰相将个人私欲与派别利益置于王朝整体利益之上,朝有弄权之相,国无“大忠”之臣。大宋朝廷失去了调节社会矛盾、应对内外打击的能力。最终,女真人兵临城下,结束了这个可耻的时代。
是的,我要讲的,是一个有关衰亡的故事,是北宋的政治文化由盛转衰的历史,而司马光是贯穿其中的叙事线索和核心人物。
宋朝历史中的很多事件和人物,貌似尽人皆知、题无剩义,实际上人们所了解的,只是一个从开头到结尾的简单轮廓,至于特定开头是如何走向了特定结尾的,中间过程如何,“相关各方”的选择如何,彼此间是如何互动的,我们即使不能说是一无所知,也是知之甚少。现时代史学研究者的任务,我以为,就是通过扎扎实实的研究,尽可能地揭露细节,通过细节展现过程,接近真实。
十六个月的“司马相业”,导致了后世对司马光评价的两极分化,爱之者视之为悲剧英雄,不吝赞美;恶之者斥之为顽固保守,大张挞伐。认识分歧冰火不容的双方,却拥有共同的认识前提,那便是,这十六个月的司马光得到了太皇太后的绝对信任,拥有呼吸之间成祸福、改变一切的洪荒之力。
然而,“细节”却告诉我们,在执政的最初九个月当中,司马光其实是“什么也做不了”的。首先,中央领导集体人员构成新旧力量对比悬殊,司马光一派处于绝对弱势。其次,神宗元丰改制所创造的“三省宰相制”给司马光所提供的施政空间极其有限。元丰新制把宰相府一分为三——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三省长官俱为宰相,按照政务处理程序分工,中书取旨,门下复核,尚书监督执行。三省宰相中,中书省长官负责上奏皇帝听取最高决策,稳定拥有议政权,实际上把握着“政治的权柄”;而司马光只是门下省的第二把手,他的盟友吕公著是尚书省的第三把手。在“三省宰相制”中,根本轮不到他们说话。最后,司马光和太皇太后都缺乏抛开体制、另起炉灶的能力和意愿——太皇太后是政坛新手,初学乍练,缺乏经验;司马光骨子里尊重体制,缺乏像王安石那样的魄力。这就是“司马相公”的体制困境(本书第32章)。
九个月之后,神宗旧相中最具影响力的蔡确、章惇外放,高层人事调整结束,理应提倡和解,打破新旧间的芥蒂心结,从思想上解放在神宗时代成长起来的绝大多数官僚,集中力量致力于政策调整。然而,大宋朝廷却无力完成这一转变。太皇太后在“政治实习”的过程中,与台谏官之间建立了更为紧密的信任关系。台谏官的年辈和职务特征让他们更倾向于从教条出发,非黑即白,夸大对立,鼓吹仇恨。在台谏官的引导下,太皇太后的核心关切转向了自身权威的维护;对于身居高位、更具全局眼光的宰相大臣,她已经不再信任无间。司马光的健康状况江河日下,日益陷入有心无力的境地。吕公著、范纯仁极力主张和解,却无法左右太皇太后。“和解诏书”终于出台,但却删去了最关键性的内容,实际上等于一纸空文。在政策调整方面,司马光的政策主张漏洞百出,章惇的批评合情合理,可是,被“政治正确”蒙住了眼睛的朝廷却选择“站在司马光一边”。被政治纠葛高度扭曲的政策选择,已经无法因应政府和社会所面临的真实问题。北宋政治,除了可耻的堕落,不可能再有其他结局。
以上种种,唯有进入细节,才能“看见”。然而,进入细节之后,我们难免会由衷感叹“偶然”对历史发展的塑造力。比如,仁宗与英宗的关系,倘若英宗是仁宗亲子,或者倘若仁宗对英宗的承认来得不是如此艰难被动,那么,英宗朝及以后宋朝政治的走向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再比如,倘若张方平的父亲不是那样长寿,偏偏在儿子被任命为副宰相之后离世,那么,以张方平的能力,他一定能担当起整顿财政的责任来,而王安石也就未必会获得神宗的信任和重用。仁宗无子是偶然,张方平丧父是偶然……无数偶然的碰撞,最终铸成了实然,这便是我们看见的历史。
二 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
倘若只是揭露细节、展示“偶然”,本书传递给人的信息则未免太过悲观,仿佛人只能做“偶然”的奴隶——当时人逆来顺受,后来者徒呼奈何。“偶然”的背后,还存在着非偶然的结构性因素,这便是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
北宋政治是皇帝制度下的王朝政治。皇帝制度之下,王朝政治以一姓统治的长治久安为最高目标,追求一个“稳定”——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两个“安全”——朝廷国家的统一与安全和皇权的安全。为达此目标,王朝政治的“理想状态”应当包括下列内容:第一,国家制度的设计倾向于地方、部门、机构、个人的分权制衡,以确保皇帝和中央的集权。第二,政策制定要避免对社会的频繁骚扰和过度压榨,以“不扰”为善政,皇帝与朝廷国家必须承认并敬畏社会所具有的“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集体力量。第三,在政治运作中,一方面,皇帝应当保持其超越性,克制私欲,不受制于任何利益群体(比如后宫、外戚、宦官;权臣;勋贵;强藩),并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兼听独断;另一方面,士大夫要能够有效地辅助皇帝治理国家,这种“有效的辅助”不仅仅是作为行政官员承担治理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及时纠正皇帝的错误缺失,提醒皇帝统治中可能存在的治平隐患,防患于未然,弭患于已发,消除小矛盾,避免大冲突。
以上述标准衡量,截止到仁宗朝的北宋政治,已接近于“理想状态”,取得了皇帝制度下王朝政治的“最好成绩”:第一,国家制度设计精良 ,近乎完美地实现了分权制衡,基本消除了强藩、宦官、权臣、外戚等因素对国家统一和皇权稳定的干扰,做到了“百年无内乱”。第二,政策制定顾及社会的承受能力,在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避免过度扰民,所谓“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2]第三,批评纠错机制实施有效,这套机制包括复杂精密的舆论、监察、信息沟通制度,以及包容批评的思想基础和政治风气——“最好成绩”的政治不等于没有问题,而是有问题能够被及时指出,加以纠正。
北宋政治的三项核心特征——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追求国家-社会平衡的政策倾向,以及实施有效的批评纠错机制——之中,制度设计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或者说惰性;政策倾向与批评机制的稳定性则是脆弱的,影响其稳定性的主要是人的因素,可以分为皇帝因素、宰相大臣因素和士大夫因素。
第一,皇帝因素,包括皇帝的思想、道德和心理因素。皇帝制度之下,皇帝“享有至高无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权力。来自臣下的任何限制,如果他想拒绝,都有权拒绝;他的任何荒谬决定,只要坚持,臣下都不得不执行”。[3]只要不打破君臣秩序,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皇权实施强制性约束。作为皇权的行使者,“皇帝”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作为时间序列中“列祖列宗”的延续,和空间秩序中“代天理物”的人间统治者,皇帝代表着包括朝廷国家和社会在内的“江山社稷”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他应当做出符合上述利益的选择和决定——这是“抽象的皇帝”。另一方面,皇帝又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巨大的权力让他可以任意妄为、打破一切制度和传统的约束;当然,这样一来,皇帝本人、朝廷国家以及整个社会,都将付出惨重代价——这是“具体的皇帝”。“抽象的皇帝”通过“具体的皇帝”来表达,行使皇权。如何让“具体的皇帝”更接近于“抽象的皇帝”,是皇帝制度的最大挑战。在北宋政治中,“抽象的皇帝”应当尊重政策制定中的国家与社会利益平衡原则,避免个人私欲的过度膨胀;“抽象的皇帝”还应接纳士大夫对皇权的约束,对批评采取开放态度,承认这是一种正向的力量。那么,怎样才能让“具体的皇帝”做到这些呢?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教育,包括本朝传统的熏染、儒家经典的学习和士大夫集团特别是宰相大臣的引导。当然,教育不是万能的,“具体的皇帝”的具体遭遇所造成的具体心理状态,会影响甚至逆转政治的方向。
第二,宰相大臣因素。宋朝以枢密院分掌军政,宰相府只管民事,宰相府与枢密院合称“二府”,二府长官构成了广义的宰相群体。宰相“佐天子而理大政”,“入则参对而议政事,出则监督而董是非”,同时拥有参与最高决策的权力和监督百官执行的权力。[4]因此,不管是对于国家政策的制定,还是对于批评机制的维护,宰相的想法、说法与做法都具有风向标的作用。作为士大夫集团的领袖,宰相代表群臣引导、规谏皇帝;作为政府首脑,宰相大臣本身也要有容纳批评的雅量。
第三,士大夫因素。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赋予了士大夫教育、引导、规谏皇帝的权力与责任,士大夫引用儒家经典、天意人心与祖宗法度对皇权施行约束。这种约束,就其本质而言,属于非强制性的道德约束。因此,作为一个整体,士大夫必须展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或者更确切的说,集体的道德败坏会使士大夫丧失约束皇帝的力量。衡量士大夫集体道德败坏的标准,不是个别人物的道德水平,而是这个群体是否陷入“恶性分裂”。[5]所谓“恶性分裂”,指士大夫群体分裂成为利益集团,集团利益超越朝廷国家的整体利益,成为影响个人与群体政治选择的决定性因素,集团之间党同伐异,互相攻击,甚而至于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其表现形式包括政治清洗、政治黑名单等。一旦陷入“恶性分裂”局面,“忠义廉耻”必然变成虚伪的口号,士大夫必将跌下道德制高点,沦为权势的奴仆;而皇帝也将失去超越性,不得不与更善于玩弄权势的集团结合。一个王朝也就距离灭亡不远了。
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北宋政治的逆转。当然,这一切不能只归咎于王安石,逆转的根源在英宗朝就已经埋下。漫长而艰险的即位过程造成英宗心理扭曲,行为失当。神宗少年即位,力图为父雪耻,“大有为”之心呼之欲出。皇帝因素发生变化,王安石作为宰相,只不过是逢君之欲,顺势而为。
首先,王安石变法改变了北宋朝廷国家的政策倾向。“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在朝廷国家的目标与社会利益之间追求平衡的政策倾向消失了。[6]不管变法派如何标榜“摧抑兼并”、“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7],但是神宗的府库里积攒下来的钱物是事实俱在的。哲宗即位之初,户部尚书李常算过一笔账,“今天下常平、免役、坊场积剩钱共五千六百余万贯,京师米盐钱及元丰库封桩钱及千万贯,总金、银、谷、帛之数,复又过半,”[8]总计达一亿贯以上。而这是在神宗对西北用兵、开疆拓土、长期消耗之后剩下来的钱物。变法的敛财本质不容否认。至于新法推行人员的违规操作对当地社会造成的损害,王安石的态度基本上是置之不理,只问其“实利”多少,“功状”如何。处理程昉淤田“广害民稼”案,处理王广渊在京东强制推行青苗贷款案,皆如此类。
其次,王安石破坏了宽容政治共识,釜底抽薪,撤掉了批评纠错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思想基础。北宋士大夫群体的“恶性分裂”出现在哲宗亲政以后,然论其根源,则必上溯至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本人反对“异论相搅”,主张“一道德,同风俗”。在王安石的纵容鼓励下,神宗不再承认批评是一种正向的力量,斥之为“流俗”,理直气壮地拒绝约束。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之说:[9]天变没什么可怕的,“祖宗”也不再值得效法,而一切反对变法的言论都是流俗,不值得留意。那还有什么是可以约束皇帝的呢?王安石还告诉神宗,“上身”即是“祖宗”(第13章),“活着的皇帝本人”就是“祖宗”,可以自我作古,而不必听命于太庙中的死人牌位——神宗被彻底“解放”了,皇权被从无形的笼子里放出来,北宋政治从宽容走向了专制。
神宗朝的专制,按照时序,首先表现为“皇帝支持下的宰相的专制”;然后表现为“皇帝的专制”,宰相沦为高级秘书。南宋政治中特别突出的“权相”现象,即滥觞于此。这两种专制在本质上都是皇权的专制。正如刘子健先生观察到的,“从北宋末到南宋,原本分享的权力逐渐被皇帝和权相集中起来,官僚参议朝政的空间近乎于无,沮丧越来越普遍地成为士大夫的典型心态。”[10]
最后,以逐利为目的的政策倾向,斤斤计较的赏格罚条,过度依靠法度、忽略道德、抹杀官员个人能动性的用人方针,培养出工具性极其突出的“新官僚”,他们服从、高效、无心肝,只关心上之所欲,不关心下之所苦,其极端典型是神宗御笔亲题的“内外理财之臣未有出其右者”[11]的吴居厚。如学者指出,“官僚像商人追逐利润一样将新法推广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日常所面对的正是利益的算计和官位的升迁。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新的士风开始形成。”[12]仁宗朝欧阳修那种“但民称便即是良吏”的为官理念,和“不见治迹,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的行政作风,[13]一时烟消云散。
神宗与王安石相得“如一人”的千古君臣知遇,被当时的宰相曾公亮叹为天意。这天意的背后,是君臣间共同的思想基础——王安石与神宗都受到法家的深刻影响。南宋的李焘作北宋编年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即位之前,神宗曾亲自抄写《韩非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王安石和神宗共同造成了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
我希望让学术的回归学术,以朴素的历史学态度来观察“王安石变法”——把它“回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看做法,看结果。王安石的新法中有很多从“现在”看过去显得非常“先进”、“具有现代性”的做法,比如青苗法像小额信贷、免役法像现代税制,然其本质却是似是而非的。倘若“混淆了历史时代的界限,任意地把古今中外的事物拉扯在一起”,所得的解释就必然是“不伦不类”的。[14]把新法中的某些做法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提”出来,用现代的逻辑去解释、包装,这种做法,是打着历史的旗号反历史,必须警惕。新法是由朝廷制定的国家政策,政策要实现,必须作用于社会。因此,要评价新法,必须看它在当时的实施效果,包括对朝廷和对社会两方面的效果。总体而言,新法具有强大的敛财功能,与民争利,“富国强兵”。但是,综合目前已知的材料和研究成果,似乎仍难断言新法在多大程度上对宋朝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破坏;个人认为,王安石和神宗的做法对于宋朝最大的损害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文化方面。北宋政治走向了皇帝和宰相的专制,士大夫参政空间被极度压缩,批评纠错机制失效,腐败横行,朝廷国家因而丧失了因应内外打击的能力。国破家亡的惨剧虽然发生在徽宗-蔡京治下,根子却在王安石与神宗。
为了方便大家利用电子书更好的学习,精心整理了网络上的各种电子书,有PDF版本的,也有TXT版本的,现有一万多本PDF的,七万多本TXT的,还有精心整理的天涯神贴,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中,有需要的可以点击下面的衔接或者扫码下载: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CSNhmbK1U4UWVtzkPcjuWA?pwd=0000 提取码: w3m9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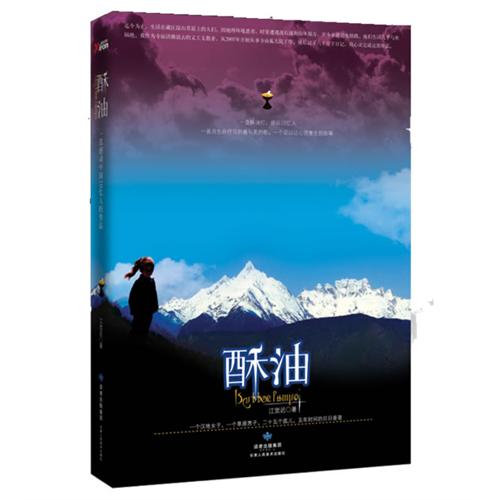


请先 !